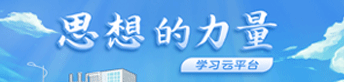学人小传:
钟甫宁,广东梅州人,1951年出生于南京,1989年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特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顾问。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委员会高级专家、南非政府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顾问、江苏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村发展。先后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6项、国际合作项目10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SSCI收录14篇。
主要奖励与荣誉称号: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其他部省级教学科研成果奖12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以及农业农村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社科名家”、江苏省“优秀研究生教师”、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学科梯队带头人等称号。
个人自述:
认真做学问的人既要入世也要出世。入世,才能使所学契合经世济民之目标;出世,才能使所行超越功名利禄之羁绊。
快乐童年打下基础
记者:回顾儿时,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钟甫宁: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不仅物质匮乏,而且父母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但生活仍然是快乐的。我们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玩具、遥控玩具和益智玩具,丢沙袋、拍洋画、打弹子也可以让我们乐此不疲;没有ipad、kindle和电脑,反而让我们更乐于读书和人际交流、更乐于走向户外。没有压力、相当充分的自由不仅给人以快乐的感觉,而且有利于兴趣和爱好的发展,也有利于智力的发展。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也许是我潜移默化接受了学前早教的重要原因。不过,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父母提前对我进行正规教育的印象;提前接受教育的原因更可能来自于同辈人的互动影响。同一个大院里居住的亲戚有一个小孩比我大两岁,也比我早两年上小学,记忆中我似乎把一道做作业当作游戏,因而自然而然比同龄人早两年接触小学课程学习内容,也多多少少培养了一些自学的能力。从1958年进入南京市建邺路小学,到1966年“文革”打断我在南京一中的初中学习,8年中小学教育期间的正规课程学习一直轻松愉快,并且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课外阅读和各种有益的活动。
记得我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阅读长篇小说,阅读面很广。当年我们阅读的科普著作包括一些介绍农业生产知识的通俗读物,其中有一本书中猜想对小麦的根部施加机械刺激可能促进小麦分蘖甚至诱发多穗,这一猜想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说服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家中园子里划出一小块地供我们“做实验”。很明显,缺乏指导和监督的游戏持续不了多久,“实验”很快就无疾而终,具体时间和原因都无从回忆了。
记者:您当时上过什么兴趣班吗?
钟甫宁:当年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无论是学校、区少年之家还是市少年之家,都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但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大多数兴趣班。那时的课外活动小组不收费,更没有功利主义的目标:既没有补课性质,参加其他各种活动也不会获得中考或高考加分。因此,家长和老师也不干预我们自己的选择。记得我曾经先后参加过建邺区少年之家的中国象棋兴趣班和鼓号队,五年级以后参加了手旗队。
手旗通信本来是舰船之间以及舰船与码头、基地之间联络的一种实用技术,在我们的课外活动中变成了一种竞技体育运动:两个人一组比赛用手旗收发报的速度和准确性。对于收报者来说,无线电收报者一边听一边记,只需要把听到的字母准确记录下来就行了,而手旗信号的接收者必须在收看手旗信号的同时,把前面已经收到的手旗信号所代表的字母连结成字、词并且记住,整句报文收完以后再完整地写下来。因此,手旗通信对记忆力特别是短期内的强记忆力要求很高,需要长期的持续锻炼。
当时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玄武湖航海俱乐部训练,寒暑假也经常去。虽然可以报销公交车票,但我们通常都步行,途中顺便练习强记能力:一个人随口说上一串40-50个字的话,另一个人立刻重复出来。高强度的训练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同时还帮助我们提高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思维的敏捷性和反应能力。短短十几秒或数十秒钟决定胜负的竞赛,容不得哪怕0.1秒的疏忽或大脑突然“短路”。我一直相信我的大脑思维能力终身受益于少年时代的手旗通信活动。
艰苦岁月慢慢积累
记者:从1968年11月到1978年3月,您在宝应插队近九年半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
钟甫宁:那段时间,我在江苏省宝应县子婴河人民公社卫星大队同德生产队插队,艰苦岁月中的种种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所欣慰的是,不经意中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宝贵的财富,转化为学业和事业上的独特优势。
当年的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劳动也十分繁重。当年农忙时,我也和农民一样赤脚走泥泞的田埂、挑100多斤的粪肥下水稻田,收获季节挑100多斤的粮食或者棉花走10多里路去公社所在地的粮站或供销社,每天两趟来回四五十里,有时甚至一天三趟。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干的是“技术活”:春天和初夏负责水稻的浸种育秧和棉花浸种,盛夏和初秋负责病虫害防治;作为民主理财小组长,每月一天核查生产队会计的账目,挑粮或棉花上街后留在粮站或供销社结算农业税、棉花预购定金等,都是农民眼中的轻松活。
记者:怎样做好“技术活”?
钟甫宁:1971年,我与同心生产队的冯锋同学在大队蚕桑场建了10多亩地的试验田,利用回南京休息时间与大队其他同学一道去江苏省农科院取经学习、引进良种,跟县里组织的基层技术员去兴化“蹭课”参加江苏农学院举办的植保培训班,并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农业科技大协作组。1972年回到生产队,在继续负责浸种育秧等技术活的同时积极参与大田生产的计划组织工作。
记得有一年春天,上级提倡降低水稻育秧时落谷密度的新技术,因为缺乏准备,我们生产队预留做秧池的田块面积出现了较大缺口。大队书记来检查工作,发现我们预留的秧池面积少了大约10亩,要我们耕掉10亩快要成熟的小麦做秧池。队长和社员们十分不愿意。我给队长提了两条建议,一是把偏僻地方原本荒废的几块边角地整理一下并支上水车,靠人工水车把这几块地变为临时秧池;二是早稻秧苗拔出栽插到大田以后,这几块秧池不按习惯耕耙栽秧,而是把畦沟里的软泥铺到拔秧时踩得坑洼不平的畦面上,重新平整畦面后继续用作秧池。两个办法同时采用的结果是多收了几千斤小麦,全队皆大欢喜。
幸运时代广泛吸收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后,您为何选择了农业院校,并将农业经济学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钟甫宁:以农业科技积极分子身份,依据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我只能报考农业院校。在本省招生的情况下,最好的农业院校就是南京农学院和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的江苏农学院,而江苏农学院所有专业包括农业经济学专业都只在理科招生,因而我只能参加理科考试。对于一个尚未完成初中学业又连续11年半没有接触过数理化的人来说,面临的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清楚地记得,第一天考数学,天气比较冷且刮着风,考场教室的许多窗户没有玻璃。拿到考卷以后我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天气冷,而是太激动。所幸的是,通过短期突击自学闯过了这一道考试关,时隔11年9个月,终于在1978年3月重新进入教室接受正规教育。
课堂学习很轻松,又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有充分的条件大量阅读各种学术期刊和书报。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农村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争论十分活跃,各种学术刊物上吸引人的文章很多,我可以在阅览室度过大部分课余时间。由于近十年的插队经历,加上大学专业学习提供的理论知识,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时各种理论和实践碰撞背后的原因和动力、演变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观上有兴趣、有基础、也有时间,客观上剧烈的社会变革不断提供演化中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素材,两者相结合,那几年中我从课外阅读、听学术报告和讨论所获得的学术积累远远大于课堂学习收获的知识。我一直认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平台,课堂学习只是获取知识和能力的一种途径,能否充分利用课堂以外的时间和资源才是决定大学期间收获多少的关键。
记者:您曾获得机会被派遣出国深造,这段海外求学经历,您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钟甫宁:1983年9月2日,我有机会到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经系深造。对我而言,到了曼尼托巴大学就像进入了一座宝库:有那么多课程可以自由选择,图书馆有那么多书籍可以阅读。将近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卡特(Colin Carter)教授这样的良师益友。卡特教授给我提供的研究助理职位是帮助他完成加拿大农业部委托的一个关于中国粮食生产与贸易发展趋势的研究课题。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是全球性的奇迹,因而引起国外的广泛注意和研究兴趣。
卡特教授在对我的培养过程中始终让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提供各种机会让我接触和利用外部资源,从各方大师那儿获得他自己不掌握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并且进入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学术圈子。例如,整个课题他自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即深入全面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历史从而预测其发展趋势,具体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框架、需要什么样的模型、如何找到必要的数据等,全部交给我来做,而且要在一个月之内拿出方案在加拿大农业部、小麦局、谷物委员会等各方面的专家面前答辩。1985年夏天回国调查,地点、内容等也一切由我决定。
在卡特教授指导下工作两年,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同时认识了许多国际著名学者,也结交了一些本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今后的长期发展建立了较高层次的平台。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我的硕士论文,1986年5月顺利通过答辩。1988年1月,我们合作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由美国Westview Press出版。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合作研究、共同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
承上启下薪火传承
记者:回国后,您在南农从教30多年。您认为,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什么心得体悟?
钟甫宁:教学和科研是学科发展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事业人才第一,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一切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无法成为现实,必须依靠教育百年树人;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科研,不仅教育的内容会逐步陈旧、过时,而且教育者本人的知识甚至思维方式也趋于固步自封,怎么可能培养出推动学术发展的人才?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阶段,培养的目标主要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教学科研人才,更需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学习科学研究,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推进学科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育人才,而不是做科研;在学校,教育是目的,科研是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从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关系来看,要警惕将研究生“工具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把科研作为工具或手段来培养学生,而不是把学生作为工具或手段来完成科研任务。也就是要帮助他们学会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养成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习惯,并且学会构建规范分析的框架、掌握必要的数量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打工仔”。
记者:与粮食安全相关的粮食供求和贸易是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该领域,您有何研究成果?
钟甫宁:粮食安全问题是我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我曾在《我国粮食储备规模的变动及其对供应和价格的影响》《粮食储备和价格控制能否稳定粮食市场?——世界粮食危机的若干启示》两篇文章里集中研究粮食储备对市场供应和价格的影响。与传统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储备可以在短期内稳定供应和价格;但是,从长期来看,储备及其短期作用对农户的决策和公共决策的影响可能导致长期更大幅度的供应波动。如果不能正确区分市场价格变化的原因,把长期供求失衡刚刚出现的苗头当作短期波动的结果,就可能错误使用储备作为反周期政策。
《正确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一文涉及粮食安全的定义和公共政策目标。对于公共政策的目标来说,需要保障的是居民的基本需求,还是甚至不计成本用不断增长的补贴来满足低价刺激出来的最大需求?需要保障的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还是全体居民包括高收入人群无限制购买享受补贴低价食品的需求?公共政策需要保障所有食品的低价供应吗?如何在国际贸易承诺约束条件下增加有效市场供应?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本报记者 杨丽 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