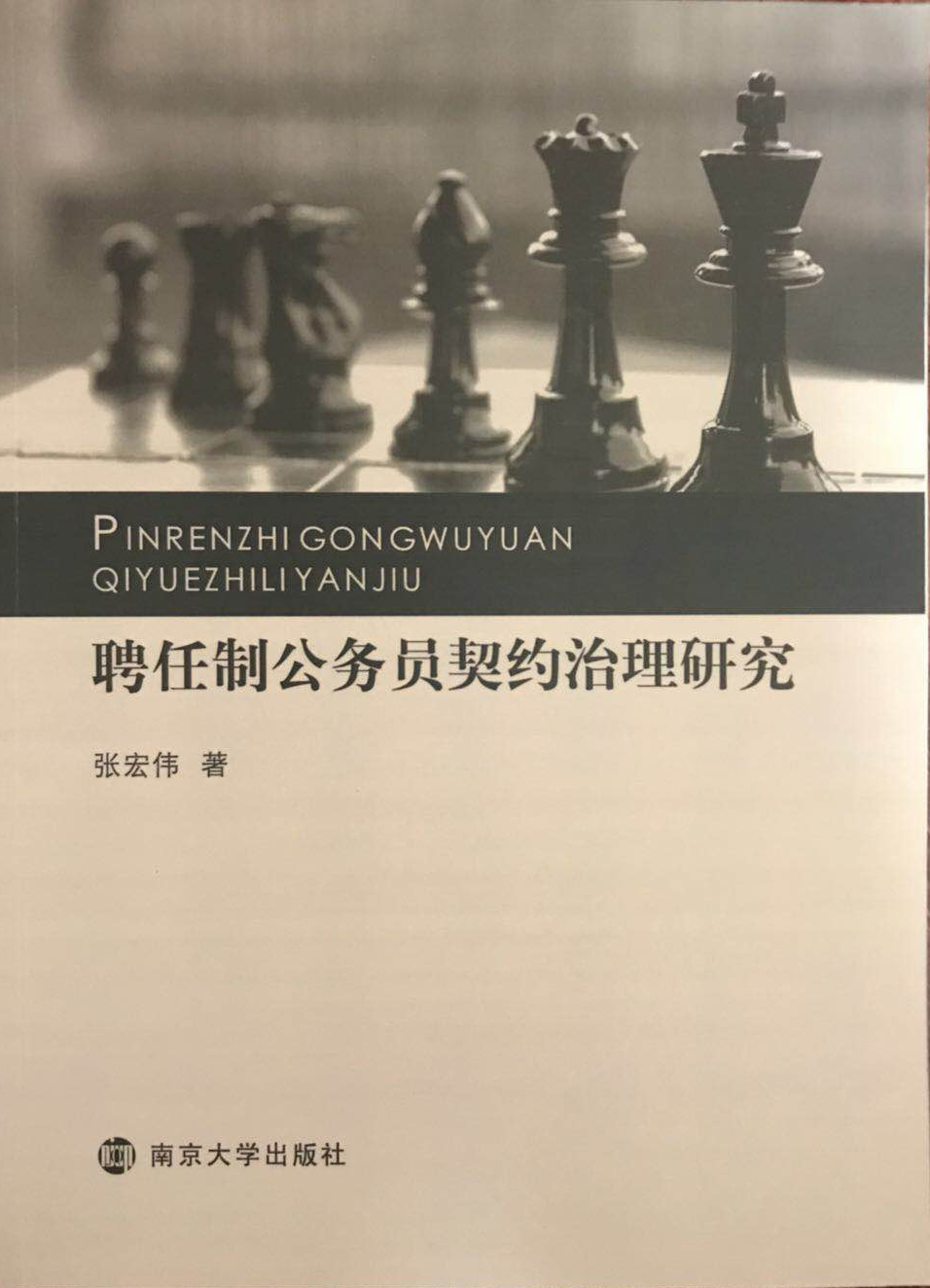什么是杂草?
最为常见的定义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也就是说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这个定义类似于某种关于垃圾的定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样定义无疑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它们是妨碍了人类的植物。它们抢夺农作物的营养,破坏园丁的精心设计,不按照我们的行为准则生存。看起来,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它们的身影。但实际上,它们并非我们的寄生虫,即便没有了我们一样可以生存。到底是谁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寻常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物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虽然会带来新的契机,但也往往会让双方都不知所措,甚至畏惧退缩。近几年,全球化浪潮似有退潮之势,“黑天鹅”不断出现。这边厢,以希腊为代表的PIGS严重拖累欧盟,欧盟的未来阴云密布。那边厢,“脱欧”公投结果显示“脱欧”支持率超过了51%,英国已正式启动“脱欧”程序。而在大西洋对岸,奉行孤立主义的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更是令世人猝不及防,并被众多精英视为全球化终结的标志。虽然特朗普宣称要在美墨边境修建the Great Wall阻挡非法移民大军在我们看来荒诞可笑,但是别忘了他的选民基础正是美国广大中低阶层群众,他是在以人民的名义高擎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大旗。
阅读理查德梅比所著的《杂草的故事》,你会发现反全球化者对待外来者的回应与我们对待杂草的态度十分相似。杂草的典型形象是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们抢走了本属于本土植物的空间和资源。它们的粗鄙使它们成为了植物中的底层公民。它们那往往来自异邦的出身和几乎总是异端的行径,都在不停挑战着我们忍耐的限度。这熟悉的多元文化的难题,是不是与我们在杂草生态学中面对的困境一样?
诚然,杂草的生命力确实强大到让本地物种敬畏的地步。死去的鸟胃中的杂草种子会在很多年后破土而出。农夫的裤角和鞋子上的泥巴、动物的毛皮都是杂草迁移的重要途径。英国植物学家爱德华索尔兹伯里,曾经在自己卷边的裤角里沾带的泥巴和植物碎片中培育出二十多种总计三百多株杂草。矢车菊和麦仙翁的种子可以在受到除草剂伤害的土壤里休眠三十年,而酸模的种子可以在泥土里或者其他环境里休眠六十年,依旧可以种植。一种叫做藜的植物,它的种子甚至在睡了1700年后依然可以发芽。因此,人们可能最担心的是杂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优势会令全世界的物种趋向于单一。
但是别忘了,一万年前,麦子也是杂草,但现在已经与水稻和玉米一起成为了种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也许,爱默生对杂草的定义更温暖善意一些:还没有被发现优点的植物。
《杂草的故事》建议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待这些桀骜不驯的植物,去了解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生长,以及我们讨论它们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类创新的故事。其实,当下席卷全球的创新浪潮,无不显露着杂草的特性,特别是来自草根的创意,大多有着“还没有被发现优点”的特征,而一旦站在风口浪尖,或许就是下一个阿里巴巴,下一个腾讯。
其实,我们与许多杂草都保持着共生关系,杂草是最早的蔬菜、最古老的药材、最先使用的染料,其中不少还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角度欣赏与我们如影随形相爱相杀的杂草呢?对杂草的宽容,也意味对未来无限可能地认同。
什么是杂草?杂草的定义取决于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世界亦然。
郑岩峰(作者系知名创客、南京创客空间负责人)